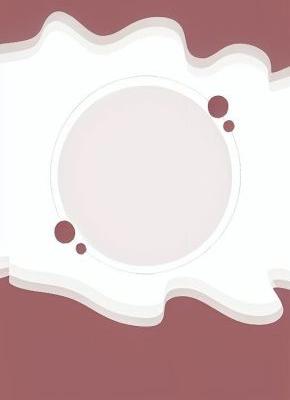
作者“作者hek4fh”近期上线的现代言情小说,是《我轮回的第八年,终于发现所有人都死了》,这本小说中的关键角色是阿哲陈涛林岚,精彩内容介绍:可没想过会遇上这种邪门的天气和路。“涛哥,看!”林岚忽然指着前风挡。浓雾边缘,隐约露出一角飞檐……
我们一行七人闯入迷雾中的幽水村。村口石碑刻着血红规则:「亥时闭户,闻水声莫应。」
「村中无活人,若见人影,勿对视。」第一夜,摄影师执意拍摄祠堂古井。
我们听到他镜头里传来女人轻笑:「下来陪我呀。」第二天,
他站在井边朝我们招手——脖子扭转180度,手背浮现青黑色指痕。
而我的日记本无端多出一行字:「别相信任何人,包括你自己。」此刻,
门外传来队友熟悉的敲门声。可我分明记得,他三小时前已经淹死在村口池塘。
---手机最后一丝信号格熄灭时,面包车正一头扎进浓得化不开的白雾里。
雨刷器疯了似的左右摇摆,刮开的扇形视野外,只剩下翻滚的、吞噬一切的乳白。“妈的,
这什么鬼地方!”开车的陈涛,我们这次户外探险小队的队长,狠狠拍了一下方向盘,
喇叭在雾里发出闷哑的短鸣,立刻被吸收了。副驾上的女友林岚抓着安全带,脸色发白。
后排挤着另外四人:玩摄影不要命的阿哲,总捧着个罗盘神神叨叨的老周,
队伍里另一个女孩小雅,还有我。导航早在半小时前就失了智,反复提示“您已偏离路线”。
我们是冲着网上那段模糊视频里,藏在黔东南深山、号称“悬棺之祖”的幽水村来的,
可没想过会遇上这种邪门的天气和路。“涛哥,看!”林岚忽然指着前风挡。浓雾边缘,
隐约露出一角飞檐,黑黢黢的,像蛰伏巨兽的鳞爪。紧接着,
更多的轮廓显现——歪斜的吊脚楼,腐朽的木板墙,
一条被荒草侵占大半的青石板路蜿蜒深入。没有灯火,没有人声,连虫鸣鸟叫都欠奉,
只有死寂,和潮湿得能拧出水来的空气。村口,立着一块半人高的石碑。
碑文被岁月和苔藓侵蚀得模糊,但用某种暗红色的、似朱砂又似干涸血液的颜料,
重新描刻了几行字,在灰蒙蒙的天光下,
触目惊心:幽水村规一、亥时(晚九点)至寅时(早五点),闭户熄灯,闩好门窗,
勿出勿应。二、若闻院外、廊下有水声、沥沥声、似人涉水而行声,勿好奇,勿应答,
勿窥视。三、村中祠堂,阴气汇聚,生人莫近,尤忌女子。四、村中无活人。若见人形影迹,
勿近,勿语,勿对视。五、井水可饮,池水不可近。酉时(晚七点)后,勿临水。
六、留宿不过三,三日不离村者,永为村邻。字迹殷红,笔画歪斜,
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邪性与不祥。尤其是第四条,“村中无活人”,像一根冰锥,
轻轻扎进每个人的瞳孔。“恶作剧吧?哪个缺德驴友搞的?”阿哲举起相机,
对着石碑咔嚓了几张,闪光灯在雾里炸开一团惨白,把那红字映得愈发狰狞。
“搞得还挺像那么回事,这氛围,绝了!”老周蹲在石碑前,手指摩挲着那些红字,
又凑近闻了闻,眉头紧锁:“不是朱砂……有股子铁锈和……霉味。
”他拿出那个包浆油亮的罗盘,指针刚一平放,就开始微微颤抖,然后疯了似的旋转起来,
最后死死定住,指向村子深处。“阴气重得吓人……”老周声音发干。陈涛是退伍兵,
胆气壮,虽然也皱紧了眉,还是挥挥手:“来都来了,这天气也退不出去。先找个地方落脚,
看看情况。都机灵点,保持联系。”我们沿着石板路往里走。雾气稍散了些,
但天色更加阴沉。两旁的吊脚楼大多破败不堪,门窗歪斜,黑洞洞的窗口像一只只盲眼,
冷冷地注视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。有些屋前还挂着干裂的玉米辣椒,色彩褪尽,更添荒凉。
走了约莫一刻钟,没见到半个人影,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村落里回响,
显得格外突兀、孤立。最终,我们在村子中段找到一栋相对完整的二层木楼。门没锁,
一推就开,吱呀声拖得老长。一楼堂屋积着厚厚的灰尘,角落结着蛛网,但桌椅俱全,
甚至还有个半朽的楼梯通向二楼。二楼有几个小房间,虽然简陋,但勉强能住人。
“就这儿吧。”陈涛放下背包,“两人一间,互相照应。老周,
你和阿哲;小雅和林岚;秦川,你跟我。”秦川就是我。我点点头,
心里那点不安却越来越浓。这村子太静了,静得不自然。而且,从进村到现在,
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暗处跟着,视线黏在背上,冰冷又滑腻。简单收拾了一下,
吃了点干粮,天色已经黑透。浓雾不知何时又聚拢过来,将木楼重重包裹。
我们点起带来的野营灯,昏黄的光晕勉强撑开一小团光明。阿哲兴奋劲没过,
翻看着相机里的照片,忽然“咦”了一声:“你们看,我拍石碑的时候,好像拍到个人影?
”我们凑过去。照片是闪光灯下的石碑特写,红字刺眼。但在石碑侧后方的雾霭里,
确实有一个极其模糊的、淡淡的灰白色轮廓,像是个穿着旧式衣服的人,低垂着头,
静静地“站”在那里。可我们当时谁也没看见!“角度问题吧,雾造成的错觉。
”陈涛沉声道,但语气不那么肯定。老周摆弄着他的罗盘,指针依旧死死指着某个方向,
微微震颤。“不对劲……这里的气,是死的,又不完全是死的……好像在慢慢‘活’过来。
”亥时快到了。我们按照村规,检查了所有门窗。木质的窗栓大多腐朽,
费了好大劲才勉强闩住。门是厚重的木门,里面有一道横木门闩,看起来很结实。
野营灯被调到最暗,只留了一盏放在堂屋中央,像汪洋里一叶随时会倾覆的扁舟。
黑暗和寂静吞噬了一切。时间变得粘稠而难以度量。我们挤在堂屋里,没人说话,
只有压抑的呼吸声。不知过了多久——“嗒……嗒……嗒……”清晰的水滴声,
从二楼某个地方传来。不紧不慢,带着空洞的回音。我们全都僵住了。林岚抓紧了小雅的手。
陈涛对我使了个眼色,示意听听动静。水滴声持续着,忽远忽近,有时像在头顶天花板,
有时又像在楼梯拐角。其间,似乎还夹杂着极其轻微的、布料摩擦的窸窣声,
像是有人拖着湿透的裙摆,在缓慢行走。“村规第二条……”小雅带着哭腔,声音压得极低。
阿哲却像是被勾了魂,眼睛在昏暗里闪着光,他悄悄举起一直挂在脖子上的相机,
对着楼梯的方向,无声地按下了快门。相机屏幕在黑暗里亮起一瞬间,他低头看去,
身体猛地一震。“怎么了?”老周低声问。阿哲没说话,脸色在屏幕微光映照下惨白如纸。
他把相机递过来。照片是夜间模式拍的,一片模糊的黑暗噪点。但在噪点中央,
楼梯扶手的尽头,有一团更加深邃的黑影。那黑影隐约有个人形,低垂着头,长发披散,
似乎正“望”着镜头。而黑影的脚下,有一小片反光的、湿漉漉的痕迹。“啊——!
”林岚不小心瞥见,短促地惊叫半声,又死死捂住自己的嘴。“丢掉!快把那东西丢掉!
”老周声音发颤,指着阿哲的相机,仿佛那是块烧红的烙铁。阿哲却像没听见,
死死盯着屏幕,眼神直勾勾的。然后,
他做出了一个让我们所有人都头皮炸开的举动——他居然把相机凑到耳边,仿佛在倾听什么。
他脸上慢慢浮现出一种诡异的、似笑非笑的表情,嘴唇翕动,
用气声喃喃:“她说……井里……好看……”“阿哲!醒醒!”陈涛低吼一声,想去拍他。
就在这时——“咿——呀——”二楼,一扇我们明明检查过、闩好了的窗户,
传来了被缓慢推开的、令人牙酸的声音。紧接着,那徘徊的、湿漉漉的脚步声,
变得清晰起来。嗒……嗒……嗒……一步一步,走下楼梯!夜营灯的光晕边缘,
楼梯口那片黑暗,浓得如同实质。“闭眼!都别往那边看!”老周嘶声道,
自己先紧紧闭上了眼,手里攥着罗盘,指节发白。我们全都照做,死死闭上眼,屏住呼吸。
心脏在胸腔里擂鼓。脚步声停在了堂屋入口。
一股阴冷、潮湿、带着浓重淤泥和水草腥气的气息,弥漫开来。那东西……就站在那里。
时间一秒一秒地爬过。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不知过了多久,
那阴冷的气息开始移动,似乎穿过了堂屋,走向另一侧。然后,
是后门方向传来极其轻微的“咔哒”声,像是门闩被拨开,又轻轻合上。阴冷的气息消失了。
又等了仿佛一辈子,陈涛才哑着嗓子说:“……走了?”我们战战兢兢地睁开眼。
堂屋空荡荡,只有那盏孤灯。楼梯口的黑暗依旧,但那种被凝视的惊悚感减弱了。
后门……门闩完好无损。阿哲还保持着那个姿势,相机贴在耳边,脸上的诡异笑容却消失了,
只剩下空洞的茫然。老周一把夺过他的相机,抽出储存卡,狠狠掰成两半,又取下电池。
“**中邪了!”陈涛低声骂道。阿哲恍惚地摇摇头,没说话。这一夜,再无人能眠。
我们睁眼到天色微亮。当第一缕惨白的天光勉强透过蒙尘的窗纸渗进来时,
所有人都像虚脱了一样。“必须离开这鬼地方!”林岚声音沙哑,带着绝望。
我们匆忙收拾东西,准备原路退出村子。可当我们拉开门,走到清晨薄雾弥漫的村道上时,
却发现——找不到村口了。那条青石板路依旧蜿蜒,但岔路多了起来,
两旁的建筑也似乎和昨天记忆中的位置有了微妙的偏差。
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转了近一个小时,又回到了那栋留宿的木楼附近。鬼打墙。更可怕的是,
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,我们经过村中的祠堂。
那是一座比其他建筑更高大、也更破败的黑瓦建筑,门扉紧闭,匾额残破。祠堂侧后方,
有一口石砌的古井,井沿爬满墨绿色的厚苔。阿哲走到井边,探头往里看。井很深,
黑乎乎的,隐约能看到一点幽暗的水光。“阿哲!回来!村规说了祠堂莫近!”陈涛喊道。
阿哲却像被钉在那里,喃喃道:“她就在下面……叫我呢……”说着,他竟然解下相机,
调整角度,想要拍摄井底!“拦住他!”老周脸色大变。我和陈涛冲过去,
一左一右架住阿哲,把他往后拖。阿哲挣扎起来,力气大得吓人,眼神涣散,
嘴里只重复着:“拍照……给她拍照……”就在拉扯中,阿哲的相机不慎脱手,
直直坠向井口。“不——!”阿哲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嚎叫,猛地挣脱我们,
竟然要跟着往井里跳!陈涛死死抱住他的腰。我则下意识地扑到井边,想抓住下落的相机,
指尖只擦到冰冷的金属边缘。“噗通。”极轻微的一声,从深不见底的井中传来。与此同时,
我趴在井沿,视线不可避免地扫过了幽暗的井水水面。水面似乎晃动了一下,
倒映出井口上方我们几人扭曲的影子,还有……还有一张惨白浮肿的女人的脸,
紧贴在水面之下,嘴角咧开,正对着我“笑”!我魂飞魄散,连滚爬爬向后逃开。
阿哲终于被制服,瘫软在地,眼神呆滞,像是魂儿真的被摄走了。“走!快离开这儿!
”陈涛背起阿哲,我们跌跌撞撞逃离祠堂区域。一整个白天,我们都在试图找出路,
但村子如同一个巨大的迷宫,无论怎么走,最终都会绕回祠堂或那口池塘附近。
池塘在村子另一头,水色幽绿,死气沉沉,水面漂浮着浓绿的水藻和一些腐烂的树叶。
靠近了,能闻到一股甜腥的臭味。池塘边也立着个小木牌,字迹模糊,勉强能辨:“禁地”。
我们筋疲力尽,食物和水也不多了。绝望的情绪在蔓延。小雅一直在低泣,林岚紧紧抱着她,
眼神也失去了光彩。老周不停地摆弄罗盘,嘴里念念有词,可指针要么乱转,
要么就死死指向祠堂方向。阿哲被陈涛用登山绳松松地捆着手腕,牵着他走,
他大部分时间很安静,偶尔会突然对着空气傻笑,或者说一句没头没尾的“水好冷啊”。
唯一的安慰是,白天似乎相对“安全”,除了找不到出路和那股无处不在的窥视感,
并没有发生更恐怖的事情。那诡异的村规,仿佛只在夜晚生效。黄昏再次无情地降临。
我们不得不回到那栋木楼。这是唯一稍微熟悉、且能提供遮蔽的地方。关上门,插好门闩,
我们围坐在即将熄灭的野营灯旁,气氛凝重得像要滴出水来。“第三天……”小雅哭着说,
“村规第六条,留宿不过三……我们明天要是还走不了……”“别说丧气话!”陈涛打断她,
但声音里也透着疲惫和不确定。他翻看着手机——依然没有任何信号,电量也所剩无几。
我拿出随身带的笔记本和笔,想整理一下思绪,或者记录下这两天的遭遇。笔记本是硬壳的,
有些旧了。我翻开,前面几页是我出发前随手记的一些装备清单和路线设想。然后,
我的血液似乎瞬间冻住了。在最新的一页,空白的纸面上,多出了一行字。不是我的笔迹。
那字迹僵硬、扭曲,用的是深蓝色的墨水,力透纸背,几乎要划破纸张:「别相信任何人,
包括你自己。」一股寒意从尾椎骨直冲头顶。我猛地合上笔记本,心脏狂跳。谁写的?